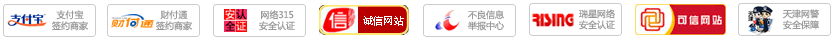【基本信息】:
作者:廖伟棠 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68421
出版时间:2014-5-1
版次:1
页数:244
开本:32开
用纸:胶版纸
包装:平装
【推荐】:
廖伟棠以诗人和作家的敏感撰写乐评,文字灵动出彩,而且大多为自身亲历,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周云蓬、左小祖咒、李志、崔健、黄家驹和Beyond、达明一派、鲍勃•迪伦……作者试图通过对音乐的评论来思考理想主义、青年文化的种种面向,比一般就事论事的乐评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全书饱蘸激情,热血感人,启人深思。
【媒体推荐】:
伟棠的音乐书写屡屡带我们越过音乐文字的新边界,抵达摇滚/民谣的许诺之地。
——张铁志(台湾知名乐评人、时评人)
主旋律听得太多,读得太多,期待跟伟棠一起唱反调。
——黄耀明(香港歌手,“达明一派”主唱)
廖伟棠的文字总是为我们导出令人欣喜的发现与独到之处的视点,同时也令我们品味到音乐与诗的共鸣。
——朱哲琴(国际知名音乐人、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
【内容简介】:
廖伟棠是作家、乐评人,也是音乐现场的亲历者,本书“一万个名字”写中国内地摇滚及民谣、“皇后大盗”写香港流行音乐、“暴雨又至”写西方摇滚及民谣音乐,均有血有肉,如置身小酒馆和排练室,亲眼目睹一个个音乐的传说起落。通过对音乐的评论来思考理想主义、青年文化的种种另类面向,使这本书异于主流乐评。
【作者简介】:
廖伟棠,70后诗人、作家、摄影家,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等,是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年度作家。曾出版诗集《少年游》、《黑雨将至》、《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十种,评论集《出离岛记》、《游目记》、《深夜读罢一本虚构的宇宙史》,摄影及文集《我们从此撤离,只留下光》、《衣锦夜行》、《波希米亚香港》、《寻找仓央嘉措》,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等。
【目录】:
第一辑 一万个名字
不合时宜的歌唱 / 3
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 10
诗人左小祖咒的愤怒 / 18
七十年代的遗孑:美好药店 / 23
春天不责备盲人 / 29
鸟写的寻鸟启事——小河 / 35
赵已然的旧天堂 / 42
当击铎采诗者开始歌唱 / 48
离魂历劫之歌——大忘杠与宋雨喆 / 55
升华的屌丝之歌——李志 / 62
万能歌谣,不万能的青年
——万能青年旅店 / 69
海丰英雄多奇志——五条人 / 76
崔健与香港 / 83
朱哲琴,向民间歌者的皈依 / 90
旧时迷笛吹奏 / 97
第二辑 皇后大盗
《一代宗师》里的香港Blus前传 / 107
少年香港说 / 114
黄耀明的另一个中国 / 121
侠隐再达明 / 129
时光之狐——周启生 / 138
香港曾有家驹和Beyond / 145
Beyond最后的超越 / 150
真正的红歌在香港 / 154
香港抗议歌谣前史 / 161
my little airport:离开还是留低? / 170
第三辑 暴雨又至
暴雨的反对——重遇Bob Dylan / 179
在地下——The Velvet Uuderground / 192
汤姆不坏——Tom Waits / 199
烟嗓子,烧刀子——Marianne Faithfull / 206
行走的小糖人——Roderíguez / 210
苦调传唱——《Violeta Parra》和《美姐》 / 217
迷失探戈——Ute Lemper / 225
孤独猴王的猴子音乐——Damon Albarn / 231
峡湾与爵士乐——李铁桥和The Source / 239
【书摘】:
不合时宜的歌唱
去电影节看纪录片《克拉玛依》,我的不少朋友都想起那一首沉重的歌:“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火灾也许难防,但坚持要比学生们先逃离的领导们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前两个星期,山西省王家岭矿难,我马上想起的还是这一首歌,“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果然,矿难未了,又有了地震,地震中大量学校倒塌,旁边的政府大楼丝毫无损,中国人的孩子,又被“豆腐渣工程”吃掉。
唱这首《中国孩子》的,就是盲人歌手周云蓬。最近一次听见周的名字,是前天晚上在香港长沙湾顺宁道,声援以露宿抗议拆迁的单亲妈妈杨柳源的音乐晚会上,年轻歌者黄衍仁唱了一首歌《永隔一江水》:“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歌是几十年前西部民谣歌王王洛宾的歌,但黄衍仁说他是从周云蓬上海演唱会上学来的,民谣的三代跨地域传承,凝结在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事件上:反抗拆迁,黄衍仁特意说出是“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这句歌词让他感触良多,放诸今日所谓民怨爆炸之香港,这句话很不和谐,却是大家的心声。诗可以怨,就是如此。
《春秋公羊传解诂》里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中国,歌的诞生就很有中国特色,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因为怨:包括饿和累。说回直接作用在歌唱者本身的现实,时至今日,流浪于中国土地上的民谣歌者仍然对饥饿深有体会,不止是精神上的饥饿,甚至肉体上的饥饿在大概十年前还困扰着他们,因为在艺术家之中,音乐家是相对贫穷的,而民谣艺术家又是音乐家里最贫穷的。但是,“诗穷而后工”,在窘迫的生存状况中唱出的歌诗往往是峻峭而最切近生存本质的。我记得,即使是2002年,还有一个刚刚从西北到北京发展的乐手,为了生存而去做送饮水机用矿泉水的工作,每送一大瓶才有一块钱的报酬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似乎和一片光彩的艺术圈格格不入,却是普遍发生在经济生态圈低层的。
但因此,“劳者歌其事”也得到了新的解释:劳动者歌唱其劳动本身,这不是主流宣传所歌唱的抽象的劳动,而是实在锻炼或者伤害着一个人的肉体的劳动,如火烘烤着歌喉,使它有真实的痛感,民谣歌者得以和普通人分享这种真实的痛感。真,是民谣歌者最突出的优点,甚至是歌唱民谣的先决条件,其次才是美和善,于是我们听到了胡吗个的外省青年进京的尴尬、杨一的漂泊者的生存妥协、赵已然的边缘放浪、香港“迷你噪音”乐队的痛与怒……不同于清醒乐队、新裤子乐队等时代弄潮儿的意气风发,也不同于许多国际电子实验家们的超然物外,民谣歌者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真挚和固执,在这个新鲜进步的“盛世”里,他们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这个不合时宜,却使得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社会低层的共鸣,如今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挣扎于低层,但仍然坚信自己少年时代相信过的精神价值的青年?是他们和他们的劳动,撑起了民谣歌唱的内容,又是他们的洁身自爱,撑起了民谣的风骨。的确,民谣是讲风骨的,这个词在当代艺术和诗歌中失落已久,却成了聆听者寻找真实的声音的密码,也成为歌唱者辨别同志的密码。在北京,如果存在一个纯粹的民谣圈子,基本上是源于十年前左右在三里屯南街“河”酒吧活动的一些青年,他们当时有的是忠实听众,有的是匆匆过客,有的是驻场演出者,甚至有的是调酒师和侍者,我们就是在“河”,第一次听到了“野孩子”、赵已然、王娟以及唱即兴民谣的小何。“河”的历史很短,演出者的风格很多,但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有性情之人,唱发自肺腑之歌。
《毛诗序》中有言:“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没有志的诗难以称之为诗,没有真性情、不懂得咏叹性情的歌,怎么能称之为歌呢?流行乐坛充斥着虚伪、无病呻吟或享乐主义的批量制作,离风雅之旨固然远得很,就连人类的基本情感的正常传达都似乎欠奉,娱乐工厂批量生产,听众也麻木地批量收货。但如果在一片靡靡之音中突然听见自己的窘迫和饥渴,会有多少人能猛回首,直面现实?
直面之后,可以选择的不一定是犬儒的妥协,最低限度可以选择拒绝。民谣歌者和其热爱者的不合时宜的骄傲,就在于可以拒绝主流社会强加于身的游戏规则。改变世界,先从改变自身开始,这是每个理想主义者都必须认识的道理,端正自身、选择清流一般的声音、清流一般的生活,然后向更广阔的世界迈步,传递这种声音和生活的态度,是我们可以一点点做到的,正如此铭:“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民谣承担了这样严肃的使命,是因为本应承担的诗歌,选择了逃避。诗不言志的时代,歌可言志。海子的《九月》经由周云蓬唱出,大气浩然,在悲壮中提醒我们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个世界不同于我们苟活的当下,那里有真正的明月、长风,有一个人之为人所必须的精神向度、终极思考。不合时宜者,最切中时弊。
【精彩文摘2】
诗人左小祖咒的愤怒
左小祖咒在杂志采访和微博上自称“摇滚师”,但他在自己的书《忧伤的老板》的第179页里却不小心透露了真实的自我定位:“我呢?是个诗人,能搞什么当代艺术?”——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说了个祖咒式小谎,他写诗、搞摇滚,也搞了不少当代艺术,而且在这几年间变得名声隆隆。但他说:“人们也许会发现,我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是个深刻的人,而不过是个捣蛋鬼,只是正好一下子撞在了他们的怀里而已。”
2001年我去到北京,最早认识的摇滚音乐人就是左小祖咒。他那时候偶尔住在诗人颜峻家的地下室,而我住在颜峻家附近,认识左小祖咒前,先见到了他的裸体——他参与的著名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照片,就挂在颜峻家客厅,这很多参与艺术家珍而重之的代表作,日后却成为了左小祖咒反讽的对象:裸体的一堆人换成了一堆猪,命名为《我也爱当代艺术》。晚上见到祖咒,他打车带我走了好几家唱片店,为了让我买到他的正版碟,车费比碟的价钱还贵,可这就是他的执着。
我们有过喝得酩酊大醉一起搀扶着回家的时刻,当然更多的是他在台上“胡喊”(他自己说的)我在台下感动得一塌糊涂——尤其他唱他那些野蛮的伤情歌的时候,比如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说过他是一个温柔和暴烈的矛盾综合体。“从《走失的主人》到《庙会之旅》到《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到《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左小祖咒完成了从一个单纯的后庞克到一个实验音乐家的转变,他野兽式的野蛮、Tom Waits式的忧郁、马戏团魔术师般的虚伪……都显得和中国当代艺术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却构成了左小祖咒的魅力的全部。”这是我在一篇关于我们时代的诗的演讲中对他的概括,的确,我也认同他是一个诗人。
他的音乐时而凶猛狂暴时而沉醉不知归路,在那些纷繁的配器中还会迷路,尤其到了最近的两张专辑,制作的精良反而削弱了他一贯的锐利。但他的歌词却犀利至今,因为他的自我反讽能力和批判力似乎是与生俱来,同时又带着戏谑、挑衅甚至无厘头,他不断拆解主流价值,也不放过自己的欲望、怪诞与虚无。
对于政治,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左小祖咒的政治抒情是反政治,他的讽刺和挖苦深刻有力,但到最后却指向虚无,天下乌鸦一样黑,甚至你我都不例外,这是左小祖咒常常强调的。而且他也反对精英和诗人这样的有所负担、被人期待的身份,而更愿意作一个自由说话的歌者,虽然常常说些古怪,甚至政治不正确的话。
他的《冤枉》就说出他的身份,他不希望被冤枉、误读:“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你企图通过短时间的狂啸来创立经验丰碑/以便打开隧道通告他们:/旅客同志们,十二节车厢已经失火,/十一节车厢的 马上就要烧到你们啦!/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身处第十三节车厢的歌者,他到底是置身事外的流浪汉,还是纵火者呢,唱那首歌的时候的左小祖咒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在《忧伤的老板》中有一首他写的诗《否则我不会杀他》,最后几句是:“假如秘密不死于自我败露/假如矜持容下牧羊人哀伤的歌声/愤怒怎会胀破我的刀鞘?”这还不是最好的宣言诗吗?
【精彩文摘3】
香港曾有家驹和Beyond
对于很多香港青年来说,没有Beyond的香港和有过Beyond的香港,是两个香港。我是在青年文化发展的层面上说的,市民审美风气保守的香港,玩乐队被称为“打Band”,九十年代之前几乎都是被父辈视为只有两种人会干的:一是番书仔/有钱的花花公子;二是臭飞/小流氓,只要看看七十年代许冠杰电影里偶尔客串出现的那些“Band友”就知道摇滚爱好者在一般公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长发、奇装、邋遢、流里流气,虽然许冠杰也是玩乐队出身(莲花乐队),但他明显属于番书仔,而且也很聪明地单飞了,只剩下弟弟许冠英坚持摇滚形象,数十年如一地穿皮衣、留Beatles头,结果只能当笑星。
真正给摇滚乐手形象“洗底”的就是Beyond,Beyond在1983年组成,最初也是长发皮衣的重金属形象,但从1985-1988年签约唱片公司渐渐从地下走到地上,形象也渐变,先变做《阿拉伯跳舞女郎》里的中东风,后变做《秘密警察》的时尚青年,并且出演青春电视剧,四人本来就长得阳光,这下终于成为了香港妈妈们也喜欢的邻家大男孩(《真的爱你》更是彻底征服了香港的妈妈)。继而黄家驹坚持在传媒面前直言,歌曲关注国际时事,明显比其他歌星要有智慧有主见,这又得到了很多耿直的香港爸爸们的喜欢,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青年。
家驹因意外离世之际,也是他的作品走向最成熟甚至酝酿新变的时候,无论从流行音乐的角度还是从流行文化意蕴的角度来看,《长城》、《农民》、《海阔天空》等作品都是相当完美的作品。因此家驹之死给公众留下一个天才夭折的遗憾,我身边很多香港玩音乐的青年都记得,从此父母不再嘲讽他弹吉他,只是跟他说要向家驹学习!
今天很多香港乐队或者流行音乐创作人,因此都曾受惠于黄家驹和Beyond,无论后来他们走向前卫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毕竟Beyond用自己妥协的方式,给香港文化划出了一个空间:摇滚音乐获得一种对世俗香港而言恰到好处的“合法性”。达明一派是比Beyond艺术性高太多、思想性也深刻很多的乐队,但因为远远超前于香港人的接受程度,反而是到了激进的九七后甚至本世纪才渐渐彰显出他们的公众影响。
香港曾有Beyond,这也是整个粤语地区的幸运。对于更为世俗化的广东地区,许多“70后”青年第一次认真思考“理想”二字来自不是教科书里的陈腔滥调,而是有血有肉的呼声,可能就是来自黄家驹的微沙嗓子。家驹的嗓音独特,非常诚恳、温热,但又有Blues歌手的从容唱叹之自由感,绝不是如某刊写手所说的人皆能模仿的普通嗓音。如果给他一把木吉他让他自弹自唱,他会是香港的Neil Young。
那个时代我们的确都没见过世面,不只是某写手说的二三线城市,北京香港青年都没见过多少世面,所以特别庆幸在成长最尴尬的青春期遇见的是黄家驹和Beyond,而不是后来一点的柔情蜜意四大天王或者无数享乐主义小天王小天后。正如我在黄家驹逝世十周年自己的纪念文章所写:“如果没有家驹,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个反叛少年,他却为我带来了一个反叛者起码的价值观:和平与爱、人的平等、对理想的执著……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简单,但对当时一个惨绿少年来说,那几乎是感召,让我们知道了反叛不能无因、自由需要担当。”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叫普世价值,Beyond的歌为没见过世面的我们埋下了它最早的种子,虽然有点简陋,但是种子都是简陋的。然后他们的音乐虽然从早期的Art Rock变成了后来的Pop Rock,但他们坚持只唱自己的歌,这也是一种当时乐坛难得的态度,第一张《再见理想》和最后一张家驹尚在的《乐与怒》依然是出色的跳板,我从此出发走向东、西、南、北,我以宽容的态度拥抱那些比Beyond复杂、深刻的罗大佑、Bob Dylan、Nick Cave、崔健,因为我记得家驹教过我:音乐口味要杂,摇滚精神要宽容,而且音乐人要关注世界。
家驹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哥哥,能引领你走小小的,但是关键的一段路,然后他停下来,微笑地看你超越他。香港曾有家驹和Beyond,我并不羞于承认今天听实验摇滚、前卫民谣和自由爵士的我曾经认真聆听他们,就像一个诚实的人从来不会否认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一样。
【精彩文摘4】
暴雨的反对——重遇Bob Dylan
一
我听见有雷炸响一个警告
有浪咆哮要把整个世界淹掉
听见一百个鼓手双手在燃烧
听见一万个人在耳语但没人在听
听见一个人将死于饥饿,听见人们对他大笑
我听到一个在阴沟里死去的诗人的歌声
一个小丑在后巷中哭叫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而暴雨就要下起——
这是Bob Dylan最伟大的一首歌《暴雨将至》(曹疏影译),他所唱的也许是当时的美国、古巴、苏联,也可以是今天的日本、西亚、北非……一切意象那么清晰强烈,而咆哮之语又如暴雨迅即混和了大厦将倾之声,含混而至于拥有超越时代的力量。对于十多年前刚刚接触他的我来说,他是二战后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不落言诠,却直指激荡燃烧着的青年灵魂。
1995年第一次听到Bob Dylan的一张完整专辑之前,我已经在诗人袁可嘉编的一本外国现代诗选里读过他的歌词,我记得袁老写到在美国听Bob Dylan演唱会的盛况,把Bob Dylan比喻为柳永,写得像有井水处就有Dylan歌似的。袁老把Bob Dylan的歌词作为诗翻译过来,放在那本大师云集的诗选里居然毫不逊色,而且另有一股洒脱涤荡之气,且神秘、猛锐如春夜之虎。
我曾直接师从他的歌而写我的新诗,这首先是一种意气风发的精神,我来了,我看见,我唱出。一个最敏感的心坦然直面最晦涩疯狂的现实,像美国当代诗歌,拥有一个消化一切的胃,世界于是向他敞开——在我最初的理解中,Bob Dylan就是这么一个魔术师一般的吟游诗人。但是即使是十五年前单纯的我,也从Bob Dylan处学习了不单纯以及批判。坦荡之气骨与神秘繁复之意象,是他的两面,在现代诗中很少有人能综合之,除了洛尔迦——由此也可以看出影响Bob Dylan的,除了迪伦•托马斯,还有洛尔迦和布莱希特。 Dylan和他们的叙事歌谣和我们的《诗经》、乐府有同样珍贵的质量:直接、纯朴又婉约、新奇,他们教会我如何以诗歌的形式叙事而不是藉小说、戏剧的形式叙事。
就像一个诗人的诗风发展变化一样,Bob Dylan的歌词像他的人生、他的音乐一样变化多多,变化不大的是技巧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意象营造为主,但关注主题从由Woody Guthrie而来的对美国底层生活的关注,去到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人民抗争,他忧时愤世但又冷言调侃,充当的是一个类似莎士比亚戏剧里小丑的角色——他们是最辛辣的行吟诗人。
但从《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这张专辑开始他开始为自己写作,走进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并且流露出他日后越发凸显的反对姿态:反对听众和评论家对他的强行定位,甚至还反对自己。把他的反对姿态与介入时代两者结合得最好的是随之而来的两张插上电吉他、“背叛民谣”的《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和《Highway 61 Revisited》,那里面句句是内心幻象但又让人深切地感到时代之痛。此后Dylan还在这样的路子上若即若离地走了很远,除了曾经因为成为“再生基督徒”而让1980年前后几张专辑带上宗教色彩以外,他的歌词依然保持一贯的怀疑主义精神,也保持一贯的优秀现代诗水平——因此前些年他不断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我一点也不吃惊。
Bob Dylan还在写下去,以歌、以诗、以回忆录甚至小说的方式,他时而回去民谣草莽之根,时而狂奔到兰波的幻象国度,时而则在摩登都市的雾与人海中浮沉……这些都是他质问自己的方式,他也越来越乐于在自身的深渊里畅泳,喃喃自语而不管我们是否能听懂。但就像我十五年前写的一首献给他的诗《六十年代的老巫师》结尾所说:
紧靠着他一点沙哑的灰烬
远离六十年代和残余的中年肚子
在偏僻的北京或香港
紧靠着,紧靠着他一点破裂的词语
青年们被吃剩的翅膀骨头无法入睡。
——被他唤醒的我们,本身将构成他最多义、有无限变奏可能性的一首诗。
二
我生也晚,错过了那个抗议与爱的时代。第一次听到Bob Dylan的一张早期专辑时,Dylan的声音让我吃惊,二十出头时的嗓音已经老韧如一个饱经江湖的老海盗。听着那仿佛对这个世界毫不买账的嬉笑怒骂,你不得不承认,他早已历经沧桑、熟悉时代的赌局。那时的Bob Dylan对我最富有魅力,他既是如他所唱的Mr.Tambourine Man一样是一个神秘的引领者,又是《暴雨将至》中那个与你一起走进黑暗森林的战友。他的音乐则从利落直率的木吉他口琴式布鲁斯,发展到电流激荡的民谣摇滚,甚至还带上六十年代不可缺的迷幻气味。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Bob Dylan,一开口就是风起云涌。
和其它听Bob Dylan的前辈不一样,我是同时接触六十年代激进的他、七十年代反思的他、八十和九十年代“堕落”的他的。但因此我能拥有一个最多面体的Bob Dylan。从1961年,《Song to Woody》的淳朴刚毅;1962年,《Blowin in the Wind》的愤怒哲言;到1963年,《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前瞻号召。到民谣时代结束,电流像更多变的意象和节奏使诗歌涅槃重生,1965年的《Mr.Tambourine Man》仿佛彩衣魔笛手开启了一代人的迅猛幻想;《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g)》的犀利反讽;《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和《Like a Rolling Stone》的虚无和绝望;《Ballad of a Thin Man》一针见血的质问;直到《Desolation Row》那史诗式的疯子方舟受难图!这个时期的Bob Dylan俨然是我最倾慕的冷面骑士。
后面纵还有《Blonde on Blonde》的晦涩自辩、《John Wesley Hardin》的幽怨与释然……Bob Dylan却慢慢离我远去,走回他自己的封闭世界中去了。他最后一次以歌声打动我,已经是1993年那张《World Gone Wrong》和1995年那张《MTV Unplugged》,又回到一个人和吉他、口琴的纠缠而生的根源布鲁斯,居然还有火气和血的味道,又有沉淀它们的力道。
但他很快就真正地老去,进入万马齐喑的八十年代之后更是锐气尽失,交功课一样交出来的一张张新专辑没有一张能有当年的惊喜。我在一个抽离的时空中同时听到不同年代的他,渐渐困惑:此Bob仍是彼Bob耶?慢慢我也在聆听的道路越走越远,走到实验音乐与爵士乐的庞大迷宫去了,Bob Dylan日渐生疏。转眼是2005年,我在北京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认识老年痴呆症》的书,封面竟然是不知从哪里盗来的老Bob Dylan头像,我几乎怒而泪下,你叫我情何以堪!那个时候,我的二十多张Bob Dylan专辑已经在旧居尘封许久。
为了迎接我的铃鼓手先生来港演出这一夜,我搬出了我唱片架上放于最显赫位置的二十三张Bob Dylan的各种专辑来重听。 Dylan魔力依旧,沙哑嗓子仿佛依然吞吐着云彩与大海。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在一个澳门电台的午夜节目“另类音乐接触”听到Bob Dylan,我已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谣歌手,要听懂他的歌,需要配备一书库的二十世纪理想主义兼虚无主义精神读物作为后盾。下面开列的书单,都是我读过的书,他们帮助我理解了产生Bob Dylan的那个火与爱的时代,也帮助了我理解Dylan。
首选当然是《狄兰•托马斯诗选》,就是因为倾慕这个二十世纪最天才的威尔士诗人Dylan Thomas,Robert Allen Zimmerman才会改名为Bob Dylan并以此扬名后世,Bob Dylan从狄兰•托马斯处学到最深刻的是对死亡的思考以及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幻想戏法,狄兰•托马斯比Bob Dylan浓稠很多也更黑暗,他身上更多二战的烙印,如此炽热疼痛以至于诗人在三十九岁便酗酒而亡。
二是《夜幕下的大军》,六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顶峰——“进军五角大楼”事件的文学副歌,《裸者与死者》作者诺曼•梅勒以亲身经历加以小说化的“新新闻主义小说”代表作。一代青年的愤怒、迷惘与失落在克制的语言背后悸动。 Bob Dylan和Joan Baez也参加了游行,并演唱《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与《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这两首歌曲。
当然少不了Bob Dylan回忆录《像一块滚石》,无论我们热爱、错爱还是对他因爱成恨,都要听听他自己的辩护词,这是他唯一的回忆录,呢喃回忆文字如意识流小说,讲述的是时代侧面的大雾弥漫,音乐背后的自我拷问与挣扎,是另一种时代的噪音,迷离以致绚烂。
而在格雷尔•马库斯的《老美国志异》里,Bob Dylan仿佛一个老巫师(虽然其时只有二十出头),敏感地感知了六十年代中“美国梦”的激变,《老美国志异》记载的就是这个特殊时刻,以Bob Dylan插上电吉他“放弃”民谣开始,到他秘密地在地下室“回归”民谣制造出传奇的《The Basement Tape》为终,《老美国志异》分析的表面是Bob Dylan,实际是分析隐藏在人所共知的“美国梦”后面那一个更为复杂甚至黑暗的美国精神。
重遇Bob Dylan,我依然相信他日益盘结成幽暗森林的大脑里面的真诚,纵然这真诚他只对他自己负责。他要来香港,我只犹豫了一下就买了演唱会的票,我不是去看自己的青春,不是去看神话时代的图腾,也不是去看这群终于有了怀旧本钱的老哥们一起以泪水和吹牛逼来互相取暖,我就是去看这个老得可以上《认识老年痴呆症》封面的老头,他将如何再一次反对我们所有人,在风暴眼的中心蹲下,用内心的暴雨洗刷属于他的时代和诗篇。
……
支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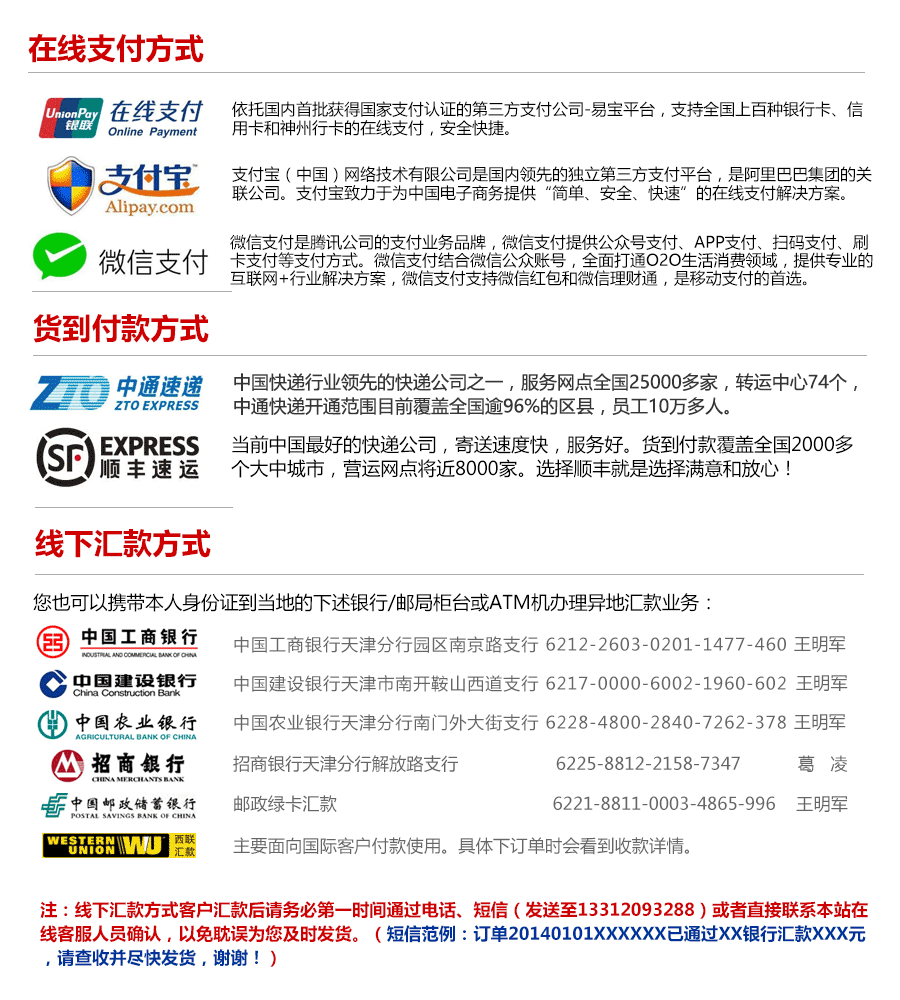
正品保证